张执浩住在黄鹤楼下三十年。他写诗,但不常待在书房,喜欢在菜场、江边,老武昌城的大街小巷漫游。
他哀悼不听话的阑尾,注视墙缝里的野草。赞美洋葱和甘蓝,偏爱油烟的味道,与日常生活同归于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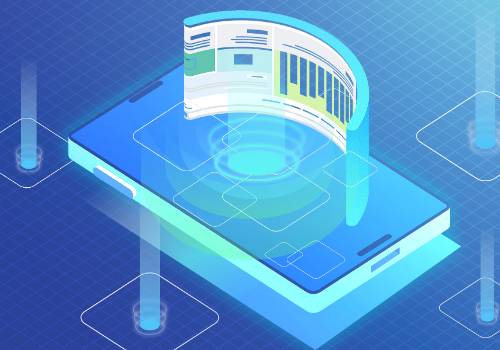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张执浩所到之处,目击成诗。以下是他的口述:
张执浩/口述
感觉今年水杉比往年绿得晚一些。
大部分时候,我喜欢在日常中寻找不起眼的物像,诗就潜藏在这些生活的褶皱中。
我写秋葵、峨眉豆、淘米水,把淘米水倒到哪里去了,全是这些东西。最近还迷上了看水杉,因为我住武汉音乐学院嘛,院子里种了一些,就天天趴湖边观察。
水杉树的叶子如果没有绽开,会觉得天空好枯燥。一旦绿叶绽开高屋顶,密密麻麻地在空茫天空中撑出一片生命的力量,就觉得很有意思。
通常,我每天早上起来会把昨天写的内容看一遍,能写就继续写,中午休息。下午三点到五点准时写作,五点到六点,要么去江边散步,要么去大成路买菜回来做饭。
我买应季的青菜,鲜活的鱼,有时跟菜市场的摊贩聊天玩,卖的豆腐哪来的?
我年轻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,完全不入世。每到黄昏,如果我夫人和她姐姐见我不在家,她们就怕我跳江去了。
那时特别叛逆,反抗命运,认同昆德拉的“生活在别处”,觉得这日子怎么过啊,生命太平庸了。
我1984年去华师读历史系,1988年毕业回老家荆门,成为现在荆楚理工学院创办人之一,在学校待了一年多,又跑到海南一个股份制大企业去待了8个月,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合做生意,然后1991年就重回武汉,开始在音乐学院当老师。
有了孩子之后,特别是她6岁到10岁时,我独自抚养她的这四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。
当时我夫人在扬州读博士,我在附中当文化部教研室主任。每天要上课,也要接送孩子,被迫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。
我开始变得特别会做卤鸡蛋,特别会炖筒子骨汤,女儿实验小学的老师小周每次来家访,都要来吃我做的这个套餐。
后来女儿在省实验读高中,我就会在她晚自习之前,把饭做好,从音乐学院大门出去,走过解放路,再拐到中华路,准点准时到她校门口的一个梧桐树下等她出来,“像一个托钵僧”,坚持了三年。
送饭路上我也会给自己找乐子。有时记步数,到工商银行多少步,到司门口天桥多少步。有时记时间,几点从家里出发,几点到学校,还写过一首《从音乐学院到实验中学》的诗。
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走路,以音乐学院为圆点,方圆万步我都走了无数回。省实验、昙华林、水陆街、江边、菜场,总在走来走去,熟得要命。
我小时候在荆门农村生活过,后来在城市里几十年,触摸不到自然界的变化,那是很痛苦的事情。 人一定要保持对自然的敏感知觉,知道这个时间田野上在开什么花,有什么菜,不能完全靠想象度日。
菜必须自己去买去做,那样一种热情会保持内心的鲜活。大菜小菜我都会做一些,喜欢琢磨。再还喜欢买一些餐具,买碗买锅,买得我老婆都烦了。
我家钟点工每回来打扫都问“这锅你还要不要”,我说不要,拿走吧。好多次买了不用就叫别人拿走,这是个病态,我自己也发牢骚,怎么这么喜欢买锅啊。没办法,热爱生活嘛,我经常说,你拿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毫无办法。
我最近有一首诗叫《像我这样的人》,大意就是,我空着手进菜场,拎着几个五颜六色的袋子出来,穿过巷子,落日正在落,意犹未尽地落下去。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再回一次菜场,买点别的东西。然后往回走,看到一个三轮车,三轮车上装了很多干货,有卖小麻鱼的,8块钱一两,我买了一斤多,同样意犹未尽。
这就是“像我这样的人”,我的生活就是这样,特别日常。 我可能是中国烟火气最重的诗人之一,和武汉这个城市的气质很像。
三年前的某天,我出门去汉阳门散步。人非常少,一个戴着口罩的女生把下巴搁在旁边男生的肩膀上,江水无声地流动。
江湖带来的开阔的力量,只要你保持一个好的心态,一定会感受到的。
武汉也很有烟火气。这种烟火气,一定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,平起平坐的一种关系。
外地人觉得面条应该都是汤汤水水的,怎么武汉搞个热干的。有一次诗人于坚来武汉,他边笑边跟我说,“老张,我发现好奇怪,武汉人怎么边走边吃?”
我就讲,武汉人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。武汉太大了,原来交通不便,没有地铁,武昌人到汉口上班,汉阳人到武昌上班,武昌人到汉口上班,奔波去码头坐轮渡,匆匆忙忙的。干的面多方便,端上就走,他也没时间坐在那个地方悠闲地吃。
这种方式也有它的意义,对不对?它不是小家碧玉的一种悠闲,是在繁忙中催生的一种热情。 只要有热情,就是有诗意的,没得热情什么都是枯死的。包括武汉人冲动脾气大,体现的还是生活的热情。就像池莉说的,冷也好,热也好,活着就好。
我最喜欢武汉的秋天。江水无声地流淌,以前还能听到江面的汽笛声,半夜听特别好听。东湖开阔的水面让我觉得无比平静,可以在湖边坐一整天。华师的桂花长廊,满园馨香,我大学时候谈初恋就是在那。
我想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武汉,就终老在这了。
其实我以前对武汉没有那么大的认同感,这个城市太大了,你很难在这个地方找到一种主人感和身份认同感。
但是最近10年,我发现我和我的一帮老伙伴们通过自己的努力,在慢慢地改变城市的文化气质,开始体会到和城市交互的感觉。
从2012年开始,我们做地铁公共空间诗歌活动,连续做了六届,征集了3900多块广告牌,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诗歌活动。
诗歌并不遥远,它就在我们身边。能让那些上下班等地铁的人们驻足片刻,看见几句分行的文字,其实挺好的。后来我们又和武汉园林局合作,做公园诗广告牌。现在在解放公园、堤角公园、洪山公园里还能看到一些散落的诗歌。
慢慢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渗透进城市的肌理之中,就会与城市一起成长,摆脱寄居蟹式的身份和生活。
写作者最终还是要进入公共生活,不能置身事外,只是埋头写诗而已。介入的效果多大,那是我们控制不了的,但是要尽可能地介入,尽可能地让改变发生。
我在音乐学院住的这三十多年,搬过七次家,每一次都能看到黄鹤楼。
每一次看到黄鹤楼压力都蛮大。古往今来已经有无数关于黄鹤楼的杰作,那后来的诗人你还怎么写,写了也白写,写了干什么?
但是也没想过搬走,因为那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。
大约三年前,有段时间我待在家里特别苦闷,在重读古代诗歌的时候,突然想到一个问题,如果是杜甫、李白、王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,他们会怎么反应?
我足不出户待在家里找他们的史料,重读他们的作品。先试着写了杜甫,之后,我再看看李白在干什么。
写完这两人之后越写越觉得有意思,干脆从头到尾说一遍中国古代诗人,将他们的性情命运与自己的生命观投注在一起。持续写了一年多,变成了我最近的新书《不如读诗——在黄鹤楼下谈诗》。
张执浩最近出版的新书《不如读诗》,诗意解读了古代诗人的生平与诗歌写作
和古代诗人对话,被迫对黄鹤楼作出回应,也算促成了自己内心与黄鹤楼的和解。
虽然现在黄鹤楼的楼址变了,结构也变了,但是无数诗人还是认可它。它像个火炬,高擎在武汉大地,是很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我觉得武汉这个城市的气质围绕着两个词语,一个是英雄之城,第二个就是诗性之城。
如果把武汉当成一只黄鹤,英雄和诗性这两个词就是它的两个翅膀。当双翼撑开,我们武汉才是名副其实的黄鹤之城。
诗意,是由诗歌散发出来的光芒。作为写作者,他必须直接创造出来一个具有光芒的东西。这些有光的东西,能够照见我们晦暗不明、鸡毛蒜皮、杂草飞舞的日常生活,否则人生不值得一过。
早年我写诗,是被李白唤醒的。但杜甫的人格投射在我身上,与我重叠的部分更多。
杜甫是一个凡人,穷困潦倒,但完全是个赤子的形象。除了有济世报国的情怀,他对家庭的担当,对日常生活的热爱,特别是客居成都的那5年焕发出对日常生活的空前热爱,让人惊讶。很少有人能做到杜甫那样顺应时代的变化,那种力量,与生活、与现实,平起平坐。
潇洒如李白,实际也穷困潦倒一辈子。
假如你现在跟李白说,我在安徽,希望你来喝杯酒,他可能马上跑去了。但在古代,他也没什么钱,要走路,坐驴车,然后碰到大风雪,为了杯酒一走就是大半年。李白诗里写过一个“白发三千丈”,那地方我去过,在安徽秋浦河,现在从合肥到秋浦河坐车还要三个多小时。放在古代他从长安过去呢?路途漫长又辛苦。
所以说古人的生活并不一定浪漫,反而真的悲苦。 他们跟我们一模一样,也像我们现代人日复一日,甚至更加悲催地这样过活。
还好我们有诗歌。诗歌一定是对生命的肯定,人们能在其中找到活下去并给自己尊严的那一部分,找到不会畏惧的力量。
///
2003年夏天,我带着女儿还有几个朋友,从成都开车去康巴玩。
一个康巴汉子戴着毡帽坐在道路中央,敲打身边的一堆石子。所有的车停下,看他把石子敲打完。整个山坳里只有他敲击石块的声音。就是那样一种地老天荒的场景,像走到了尽头。
当时高速公路都还没开通,从雪峰上流下来清浅的河水,漫山遍野的格桑花,我一下子脱口而出:
刚好我披头散发,刚好我带着女儿,刚好30多岁到了那样一个山花盛开的地方,然后写下这首诗,在诗坛留下老父亲的形象。
2016年冬天,在洪山地铁站做诗歌活动,有个男大学生突然走到我面前说了一句:张老师你好慈祥。
我一下子傻掉了,第一次有人说我慈祥。从“慈祥”到“死亡”,这些遥不可及的词语,终会一个个找上门来替代我。
我在写出了《高原上的野花》后,出于对原有的“披头散发”的形象反抗,先剪了个光头,结果头型不好看,然后留短发留胡子。
时光已把我的情感生活变成一床“百衲被”,生命和时光都需要珍惜。
张执浩写《高原上的野花》时留有长发
但我不愿意别人把我形象固定下来。一般长则10年,短则5年我要做一次改变,包括外在形象和写作风格,我要调整,不断地调整自己。
我现在的心态调整到什么都不用多想,就把诗歌当作是与我手牵手一起往前走的一个伙伴。看自己还能往前写多久,还能写多少好东西。
至于黄鹤楼,在写完《不如读诗》这本书后,我已经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焦虑了。 现在即使我不看黄鹤楼,它也矗立 在我眼前。甚至脑海里全是,只要想到,它就出现。
长江文艺出版社微信矩阵
图文编辑 胡冰倩
责任编辑 吴蒙蒙
审 核 阳继波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标签:


